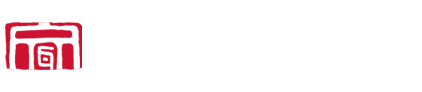40多年前,国家为何决定开启《汉语大字典》编纂工程?一代学人又付出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
四川首批156人加入编纂
川大教授徐中舒任主编
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欧洲国家圣马力诺共和国使者时,客人赠送了一套三卷的圣马力诺大词典,周恩来总理回赠了一本《新华字典》。中国素有辞书编纂传统,清代的《康熙字典》和民国时期的《中华大字典》,都曾是影响深远的辞书。随着时代发展,新中国如何改变“大国小字典”的现状?
1975年5月,“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上确定了160种辞书的编纂规划,其中便包括了《汉语大字典》。由此开始,《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正式列入国家文化建设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一部字典的编纂为何受到如此重视?

专家教授们的工作照
四川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赵振铎曾担任《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他曾如此阐释汉语字典编纂的重要性——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不需要编字典专门解释字母的来龙去脉,去说明这些字母的读音和意义。但是汉字形成的几千年来,从殷周古文到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楷书,字体多次变化,形体日趋复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字体系。几千年里,字的读音也有了不同的变革,从上古音、中古音到近代音、现代音。读音上的分歧,不是专家学者是难以弄清楚的。至于字的意义,更是纷纭复杂。正因如此,汉字研究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学问,记录汉字形音义的字典,也因此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
字典编纂工程浩大。为尽快推进该项工程,国务院决定由四川和湖北两省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BET体育365投注官网教授雷汉卿长期从事汉语文字、训诂和词汇学研究,他是第三版修订工程的执行负责人,以他为首席专家申报的《汉语大字典》修订研究课题也已入选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他曾专门了解过当年的这段历史。据他介绍,在工程确定之后,四川很快就安排了当年的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南充师范学院承编,并要求将这一任务列为各自的重点科研项目。字典编写人从哪里来?首批156位编纂人员中,大部分就是这些高校抽调的老师。此外,还包括了1975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从其他大中小学借调的老师,甚至还有从工厂、部队借调的相关人员。1976年,鉴于字典编纂工作量巨大,四川有关部门再度批准借调了50多人补充进入编纂团队。
在《汉语大字典》编纂确定以后,赵振铎主动请缨参加字典编写。鉴于字典编写动辄十年以上,需要年富力强的专家抓业务工作,赵振铎不仅很快进入字典编纂团队,还被确认为字典常务副主编。
雷汉卿介绍,当年《汉语大字典》计划收单字6万左右(实际成书收录单字5万6千多个),比《康熙字典》等所有字典收字都多,是我国古今单字的大汇编,要求尽可能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字形、字音、字义的发展。为了保证《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力争在1985年前出版,项目申请到在四川成立《汉语大字典》编纂处,作为川鄂两省编写领导小组和大字典编委会的执行机构,而德高望重的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徐中舒则在1979年被推任为主编。
团队大师云集
对字典编纂投入巨大热情
这是一个大家辈出的团队。
《汉语大字典》主编徐中舒,早年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早在上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时,他便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跟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印证,互相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徐中舒主持编写的《甲骨文字典》,堪称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

徐中舒在汉语大字典编写工作会议上讲话
《汉语大字典》的常务副主编李格非和赵振铎,同样是国内知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赵振铎的祖父赵少咸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父亲赵幼文也曾在川大中文系任教。从小,赵振铎便在祖父影响下和汉字结下不解之缘。他每天的家庭作业是读《说文》里的5个字,然后接受祖父检查。后来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开始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的系统学习,为此后参与编纂字典打下了坚实基础。
15年里,赵振铎对字典的编纂投入了巨大热情。深入编纂一线查找资料、核对文献、拟定提纲、撰写凡例……此外,他还总注意到一般辞书编纂者不太注意的方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近乎机械的劳作,他却从不懈怠。赵振铎指出,编辑出书出错的原因主要有“无心之失”和“有心之误”两种。无心之失,如校书抄书之人水平不高、抄写不慎,刻工疏忽等;有心之误,指书籍整理者因为某种原因篡改原书,这些问题必须要时刻注意,以免影响字典编纂。
李格非,武汉大学“五老八中”之一。在《汉语大字典》筹备阶段,他被任命为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制订编纂方案、物色编纂人员、协调编纂分工、起草编纂手册等,他都事必躬亲。
从1975至1990年,300多人耗时15年的艰难躬耕,最终汇成8卷《汉语大字典》的成果。字典的学术顾问、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字典出版时欣然题词,称这是一项“广搜博采 穷源溯流”的伟大工程。
与汉语大字典结缘
他们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项楚,四川大学杰出教授。1962年,项楚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考取了四川大学研究生,专攻六唐宋文学,后来在一所中学当老师。1976年,项楚被借调到了《汉语大字典》编写组,任务是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抚今追昔,项楚感叹《汉语大字典》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向学术研究的门,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正是在《汉语大字典》的十几年里,项楚得以接触到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他兴奋地发现,就在唐代伟大作家把诗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民间也有无数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创造着全新的通俗文学样式,如各种体裁的讲唱文学、歌辞、白话诗等。“它们所代表的文学新趋势,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主流。”项楚的学术兴趣,因而逐渐从六朝唐宋文学,转向敦煌俗文学领域。
雷汉卿介绍,时至今日,项楚早已是海内外著名的敦煌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文学史家和佛教学家。业内人士认为,项楚构建了古今会通、学科会通和雅俗会通可称之为“新蜀学”的学术范式,开创了包含俗语言文学在内的中国俗文化研究甚至是中国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因字典改变事业轨迹的不止项楚。还有当时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的汪春明进入编写组后便一直转行进行辞书工作,四川辞书出版社原总编辑冷玉龙同样因编写字典一生和辞书结缘。
《汉语大字典》已经是如此完备的一部字典,又为何需要重修?又该怎么修订?
“中修”字典留下遗憾
不能满足学术与传播新要求
雷汉卿表示,大型辞书一般有十年一修的国际通行惯例。这是因为字典编修时不免出现体例性、硬伤性等错误需要修订,同时需要适当增加字头和义项、更换例证等。1999年,汉语大字典编纂处、四川辞书出版社曾组织实施了字典的首次修订。经多种考量且限于当时条件,最终仅选择了对硬伤性、体例性错误进行纠正、修改的“中修”方案,在今天看来留下了不少遗憾。
“比如出现过体例的不统一。”雷汉卿说,在《汉语大字典》首版后,就有主攻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的学者指出字典编排方面的缺陷,“其中一个就是繁体字和简体字的部首归部不一,繁体字沿用的是《康熙字典》‘以义定部’,简体字则按字形归部,这就导致归部不一。例如繁体字‘褻’依据《说文》归在‘衣’部,简体字‘亵’归在‘亠’部,其实都可以归入‘衣’部或‘亠’部。1999年的字典修订版并没有一一改正,依然延续了这种编排。”
在字形上,《汉语大字典》坚持“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原则,在字头后面选列能够反映字形源流演变、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等形体,并酌情进行字形解说,“这是汉语辞书编纂的一个创举。”雷汉卿表示。然而,字典所收的古字字形主要取自《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由于成书仓促以及语料数据库条件的限制,它们在字形方面本来就存在不少问题,导致字典也承袭了错误,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疏漏。“像‘书’‘昼’‘富’‘引’‘奴’‘革’‘皮’等常用汉字缺少甲骨文字形,需要一一补充;有的出现了文字误释需要将字形剔除;有的字形摹写失真,有的字形解说则没有合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雷汉卿介绍,在体例、字形之外,《汉语大字典》还存在注音、释义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已无法充分适应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学术研究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要求。”
最终,决定重启字典修订。
对字典进行总体会诊
研究先行带动修订
字典如何修?具体涉及哪些方面?相关资料又如何收集?雷汉卿的《汉语大字典》修订研究课题,将为字典修订提供最关键的学术支撑。
事实上,《汉语大字典》出版30多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专著14部、论文1200余篇,涉及体例、字形、注音、释义、书证和疑难字等不同方面,为字典修订打下了一定基础。不过在学术界看来,这些研究仍有不少需要改进和拓展的空间。“比如注音方面现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未来字典修订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此外,字义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漏略义项、释义配例不准确、缺少文献用例三个方面,这些问题也需要纠正。”
“我们所做的其中一个重要工作,便是广泛收集整理相关研究成果,以备修订之用。”雷汉卿说,在修订字典时,事实上不可能要求编者去重新考证某个字的音、形、义。他们的职责只是正确辨析、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专人负责搜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是提高大字典修订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他的课题将专门建立《汉语大字典》修订成果数据库,为字典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进一步修订提供详实的材料支撑。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雷汉卿说,仅仅一个字形修订,就必须针对文字释读错误、字形取舍不当、字形摹写不确、来源标注有误等问题进行全面校正。此外,还得系统整理近30年出土的各时期文字资料中的新见字形,尽量全面增补《汉语大字典》选列字形中的缺环。
修订者们还要成为疑难字的“破译专家”。在大型辞书的编纂中,疑难字的破译直接影响到辞书的编纂水平和使用价值。未来,相关团队将进行疑难字考释成果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集中力量考证一批隐性疑难字,让疑难字得以确考,让“死字”激活。
“总体而言,这是一次对《汉语大字典》形、音、义研究状况的彻底测查和总体会诊,提出字典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为字典的进一步修订打下基础。”雷汉卿说。
全面修订打造精品
彰显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新时代全面修订《汉语大字典》,是用汉字讲好中国故事的源头工程,对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目前,《汉语大字典》的修订工作还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但学术界已对此寄予厚望。
每一个汉字,都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汉语大字典》是全面反映汉字形音义演变轨迹的历史性字典,需要讲清楚一个字的源流以及历史上的读音、字义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通过不断发现的新材料进行补充使其完善,便是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手段。雷汉卿介绍,《汉语大字典》很少引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作为例证。如“自”的本义为“鼻”,“天”字可以用作“颠”,在甲骨卜辞中都有例证,遗憾的是,字典没有采纳和引用。
新出土的文献尤其是简帛文献用例引用就更少了。上世纪70年代,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这些竹简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此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也是珍贵的文字资料。遗憾的是,前两版字典对两次出土简帛的引用还有不少遗漏。近年来,中华字库工程取得初步成果,不少包括简帛在内的出土文献数据库,积累的简帛文字达到了100万字左右。未来,这些出土文献材料上的文字,都将为修订大字典所用。雷汉卿表示,为了克服印刷出版物图版质量对字形清晰度的影响,他的团队将联系文物收藏单位,尽量获取并利用整理出版时的原始高清数码照片或红外线照片,尽最大可能保证使用字形的准确性。
更有意思的是,域外文献也能为字典修订提供宝贵素材。雷汉卿说,《汉语大字典》的第一、二版因条件所限,很少利用域外文献。“比如‘堗’字,在原来的大字典上意指‘灶上的烟囱’,其引用的《广雅·释室》《吕氏春秋·喻大篇》等材料,均指向‘烟囱’之意。”没想到在300多年前,朝鲜王朝中期的文学家金昌业在他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则有“室有内外炕。炕,堗也”等表述,“可见这里的‘堗’,其实是暖炕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汉字语辞典》等域外文献正是将“堗”字解释为“火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未来修订中,将在研究的基础上对域外汉字进行全面普查,并合理吸收和采纳。
这些工作将大大丰富《汉语大字典》的内容。雷汉卿表示,本次修订除了对《汉语大字典》目前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去除硬伤之外,还将适当增加字头,在遵循字典“收集从宽,入典从严”原则的前提下,对于《汉语大字典》失收的见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的历代汉字,在收字原则的管控下加以合理增补,做到宁缺毋滥,彰显字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特色。要实现这一修订目的,至少需要花费10年的时间。而未来,全方位修订后的字典,将会更准确而全面地展示出汉字的形音义演变脉络,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来源:大川微信公众号